
你的双眸深处,可有我的梦呓……
我郑重其事的在诗的结尾写下了我的感受:这是首好诗。并建议发在副刊上。几天后,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,她交给了我一张纸条:这是写给你的。写给我的?我有点不知所措。这个矜持的精灵在我的心湖里投了个石子,泛起了微微的涟漪。我回了张纸条:谢谢。周日有空吗?我有点胆怯的将纸条交给她时,她直直的望着我说:“能给我看看你写的东西吗?”我点点头。
周日我一直都等在教室里,约好外出的同学们都走得差不多了,她还是没有出现。我有点后悔给了她那张纸条。整个上午她都没来,我怀着一股烦躁的情绪回了宿舍。晚自修的时候,她的座位还是空着的。我悄悄地问她的同伴她去哪了。她的同伴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说:她姐遇上了车祸她回去了。
两天后她又回到了学校,面容消瘦了许多,整个人都失去了精神。放学的时候我故意走得很迟,她平静地坐在座位上。见教室里没有人了才说:“对不起。”我故着镇静地说:“没什么”,然后又问:“还好吗?”她无语。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。我亦无语,默默地陪着她坐着。她穿着件淡蓝色的外套,优雅得像个古代仕女。我发现她有着我喜欢的那种古典美忧伤美。
好几天后她才又恢复了往日的微笑。我们也不在通过传纸条交流了。班上的同学目光也有异样而渐渐平常。我们互相将写的诗交 给对方阅读指点,情感如秋风般自由干净。我将她的诗《姐姐》刊在了副刊上:姐姐,你睡了吗?是额头的秀发挡住了你的双眼吧,你案头那盏灯呀,映着未干的墨迹。
给对方阅读指点,情感如秋风般自由干净。我将她的诗《姐姐》刊在了副刊上:姐姐,你睡了吗?是额头的秀发挡住了你的双眼吧,你案头那盏灯呀,映着未干的墨迹。
那是蝴碟吧,翩翩的生命飞,远了……
她是农家的女孩子,家里有四口人,现在只有三口人了,爸爸妈妈都是朴实的农民,姐姐原是城里一美术班的学员,后来因为多次没考上美专,精神抑郁,整日恍惚,那时她上小学六年级。她说姐姐最爱画蝴蝶,她画的蝴蝶可美了,像真的一样,可是前不久上街时她看到了一辆迎面来的车上挂着的蝴蝶饰物,她迎了上去……
我们像风中的两只蝴蝶自由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,享受着爱带给我们的青春时光。一种情绪在彼此的心里滋生着,那是种冲动,青春的冲动。它是盲目的,它让我全然忘记了我们还只是学生,我们的行为还只能是在老师半睁半闭的目光下游弋。
那时正巧邻班的一对男女同学发生了不检点的行为,校领导甚感情势严峻,召开校会大谈肃清,全校上下风声鹤唳。而我却不失时宜地做了一件愚蠢之极的事。她的生日在十一月份,我为了给她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在校刊的中缝给她送了份祝福。可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感情的转折。
最初我是从一个平时和我有点格格不入,也在编辑室的邻班男生目光里得到这一讯息的,我至今还记得那目光里的掺着讥笑的阴森……当班主任找到我时,我已全然失去了一开始的不安,只等着最后的通谍,可当我走进班主任的宿舍时,我发现她也在那,我烦躁得想要打人。我压着心火,听完了班主任的话,其实我什么也没听进去,我一直在问自已这样一个问题,她还好吗?
她一直在哭,我愈发感到班主任的粗暴行为,我吼着:“怎么了?”班主任跳了起来……
学校里的警告处分很快就下到了各班,我也被从文学社里解了职,当主编的文选老师也对我摇了摇头。我知道我完了。我消沉了。我躲闪着人们的目光,友好的不友好的,都像针刺着我敏感的神经,我才发现我原来是这么的脆弱。我已经无心去想她了,从班主任那儿冲出来后,我一直也没想她,上课时我也尽量不让自已去看她,实际上这些天上课时我都一直伏在桌上。她也没来找我。我们都沉默了,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似的,其实那种孤寂比陌生还要来得残酷。我隐隐感到她受的伤害和我一样重,何况她一直都是那么的娇弱。但我已经无力去想那么多。
我终于病倒了。那时学校正举行校运动会,锣鼓喧天,呐喊阵阵。而我却孤单地躺在宿舍的床上,思绪离乱。我想到了爸爸、妈妈,想到了她,想到了和她在一起的快乐,但更多地想到了是失意后那份令人难以忍受的痛。我哭了,真的哭了,我又一次痛心地检验了我的脆弱,我哭得很大声,毫无顾忌地哭得很大声(我很少大声哭的,我还记得前一次的大哭是在爸爸送我来上学离开之后的事),我知道宿舍里此时不会有人在。
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时候真的会有人来。我听到了敲门声,我从痛苦中缓过神来,残存的自尊与虚荣让我有点惊惶失措,我用手拭尽泪水,一边整理好因翻身而弄乱的被子,一边猜想着来人;是她,不会,她怎么会来?我略有故意地放低语调说:“进来吧,门没锁。”其实来人已经进来了。我微闭着眼睛,但我已经分明看清楚了来人,真的是她。我感到心脏的跳动,强烈加速。
我佯装镇静,坐起身。
她问:“还好吗?这是给你的。”这时我才发现她手里拎着一袋子水果。
我说:“还好。”我的声音有点哽咽。我感觉眼圈有点凉凉的,下意识地去擦拭。她坐了下来,坐在对面的床铺上。一如以前的闲静,只是憔悴了许多,还是穿着那件淡蓝色的外衣。还是那么美。
我嗓子眼儿发痒想咳嗽,我竭力不咳出声来,我不想打破这份沉静,虽然我们彼此内心都不平静,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。可我还是咳出了声。她见我咳得难受,站起身:“要喝水吗?”我看着她满脸的温存,不忍心拒绝。我点点头。
水的热气活络得像条蛇,我的心被它缠得紧紧的充满了温馨。
她终于开了口。我原以为我们会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上一个下午,至少也是到有人来。她说:“是我连累了你。我们不要交往了!”
她说得很干脆,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这一时刻的情形,可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,我却觉得那么难以接受,甚至有点责怪她的无情。可我心里却早就有了这种说不清楚的带有妥协意味的想法。我发现我是自私的。
我点点头。我还能做什么,要求她和我一起经历这风雨吗?我们谁都经历不起,我们都很脆弱,我们毕竟还很年轻。虽然我们都不是很愿意,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万般的无奈与痛苦。可是她没有哭。她站起身说:“我走了。”走到门口。
我的心一下被揪住,脱口道:“别……”她停住脚步,突然“哇”地一声哭了,转过来扑在我身上将我紧紧地抱住,她用双唇吻着我的面颊、嘴唇,光滑的肌肤和芬香的体味使我本能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,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。我不由自主地把她紧紧抱住,任凭泪水肆意流动。两颗年轻的心不断交融。双舌不停地绞动,摩擦,狂热地品味着对方,吸吮着对方的口液,泪水。我的血液在燃烧,全身在沸腾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已,顺势把她压在身下。
当我们平静下来后,她穿好衣服,理了理凌乱的头发,没说一句话就走了。而我却被无名的恐惧所笼罩,我抓着自已的头发,不停地把头撞在墙上。我恨自已的冲动,恨自已干了一件无法原谅的蠢事。在又恨,又悔,又怕的折磨下,我的病情不断加重。最后只好回家治疗。当我重新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两个月以后,学校平静如常,我悬着的那颗心,才算放回原处。但我和她总是有意地回避对方,彼此心知肚明,我俩有一份永远不可告人的既狂热,又痛心的秘密——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过早地偷吃了禁果。但她毕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,那种刻骨铭心的初试和她走开时无声无息的背影,我发誓将永远难忘,任何时间与空间的延长与跨跃,都不能减轻我对那件事的懊恼,痛苦与酸涩、渴望与期盼无不时时在撞击着我的灵魂,可这一切只能留在自已的心里想一想,就是在最低迷、最困惑,最无助的时候也没法与她交流,也许从那开始,我们俩就像两条平行线,即便是无限地延伸,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的交合,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点,但不知怎么,她时不时地甚至会有骚扰性的光顾我的脑海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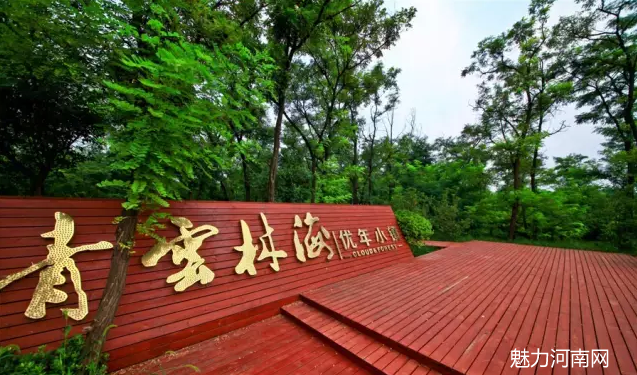
不久寒假到了。冬日里的雪封存了记忆。我们等着走进春天。
寒假里突然收到了她的信,不过信里只是最平常不过的同学间的问候。我等着新年过后才回了信,信里说了很多抱歉的话。其实我自已知道我是故意这么做的。
新学期里,周围的同学似乎对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大事都已经忘却了。我又恢复了自信。我根据寒假其间在家乡所见所闻所感写了一部长达万字的系列散文,被省报录用了。校刊也作了连载。我又一次成了焦点人物。同学们闹着让请客,我答应等拿着稿费请大家去城西的湖边野炊。
诺言很快就实现了。三月的春日还有点寒意,我们在这很孱弱的春光里尽享着天地的博爱。
她也来了。这是我意料到的,因为起初就有她的一个好同伴跟我说过让她一块来,我没答应也没反对。自从宿舍里的话别,我就警告着自已别再去打扰她,即便是在大家都已经对我们的事失去了记忆的现在,我还是一再提醒自已这一点,所以一直在有她的场合我都是尽量回避着。可我心里又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失落感。
野餐实则是“半野”,买了肉绞了馅,订了饺皮,带上锅碗筷,到这儿只需挖坑作灶台,拾干草生了火。女生们都忙着包饺子,男生们则忙着去拾柴火。一顿忙碌,一顿美餐。大家欢呼雀跃,欢笑声响彻云霄。
休息时她来到了我的面前,这是她的几个女伴故意安排的。我也不便回避什么。我们半站半倚着护堤,看着远处的天空发呆,谁也不说话。天边有着淡淡的云彩,让我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《再别康桥》: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,我轻轻地招手,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她说:“祝贺你。”
我不失礼节的说:“谢谢,你还在写诗吗?”当我话出了口,我才发现我这样问有点太唐突,我又开始后悔不该问她这些。我有些局促不安。她却显得很轻松,她说:“是的,还在写。”我怕她还会再说些什么,所以我就打住了话题。我说:“看,那船,像悬在空中似的。城西的湖该是个悬湖,远着望去就像是快要倾泻而下似的。”她点点头。神情有点黯然,不知是不是从我的不安中感到了什么。
作者简介:
刘佩金 英文名Larry,美籍华人,金融硕士,出生于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,曾在银行工作多年,当过出纳、会计、秘书、副总经理 、总经理、行长等,后移民美国,现任纽约某公司总裁。曾在国家级报纸刊物发表上百篇文章,涉及金融、经济、文学、教育等领域,著有《狂想的抉择》、《与风月无关》、《白条现象引起的思考》等,2016年10月出版了《金哥日记》,在闲暇时间里,开始了《金哥随笔》……














